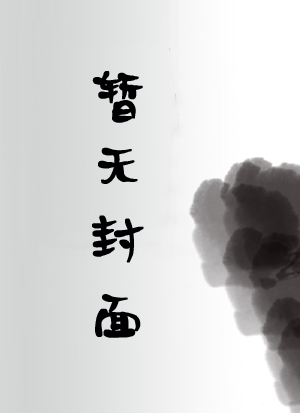徐平此話出口,衆人面面相觑。是啊,除了金、銀、絹是硬通貨,還有糧食呢。而且糧食不管契丹賣多少,宋朝肯定全收,倉庫放不下也要收。
河北駐紮着數十萬禁軍,單靠河北路的糧食可不夠。以前财政困難,河北路的稅賦奇重,加上水旱之災,不斷有人口逃亡。地方就是這樣,越是人口少了,稅收得就越重。稅重了老百姓過不下去,不住逃亡,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單從賦稅來看的話,河北的稅不重,比兩浙路一帶低多了。但由于駐軍多,差役和各種雜稅科買特别多,增合起來的百姓負擔就重了。宋朝的稅賦隻是百姓負擔的一部分,大頭在各種名目的加稅和攤派上。徐平掌三司,從來沒有減過稅,隻是慢慢取消雜稅科配。
如果契丹肯賣糧食,宋朝求之不得,最好河北和河東路的駐軍,糧草全從契丹買。這兩路當地的餘糧,存到倉裡作為應急使用,負擔一下子就降下來了。
哪怕有運河,有大道大車,糧食和草料的轉運依然昂貴無比。支撐與契丹對峙的數十萬大軍,宋朝要動用江淮、兩浙、京東、京西數路民力。與此配套的運力,還有二十多萬的廂軍和差役。從契丹買糧食,這些就全都可以省下來了。
趙祯想了好一會,才苦笑道:“河北、河東、豐勝三路加起來,七十萬大軍,這可是用來對付契丹的。契丹對此心知肚明,他們如何向本朝賣糧食?敢向本朝賣糧,豈不怕逐年增兵,他們更加難以支撐!”
明鎬沉聲道:“是以契丹才急着立誓約。誓約一立,可以約束沿邊幾路兵力,人數定死了,他們才能夠喘一口氣。兵力就是那麼多,實在沒有辦法了,契丹未必不肯賣糧。”
杜衍道:“其實以前縱然契丹不許,民間也常有人賣糧入本朝之境,并不少見。如果契丹别無生錢之道,又不能斷了互市貿易,也隻有賣糧這一條路。”
丁度道:“此管仲鬥洩之術也,契丹必有大臣知此計,隻恐不會上當。”
“此事于本朝,得之則喜,不得亦無妨。契丹願不願做,一切由他。本朝隻是要兩國公平貿易而已,此天經地義之事,天下間豈有不勞而獲的道理?北地貧瘠,能夠賣出來的貨物隻有馬匹和糧食,契丹人如果能有其他貨物賣來,自然也可。”
徐平從來不指望陰謀詭計,不是不知道計策的用處,而是萬事操之在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敵人犯錯誤上。重兵臨邊,逼迫契丹比拼國力;斷絕貿易,讓契丹物資匮乏;不許金銀銅錢流入契丹,讓那裡缺少貨币。這些措施徐平從來沒藏着掖着,契丹使節來了,也是明白告訴他們。告訴了你又如何?國力在那裡擺着。
契丹境内缺金銀,也缺銅。當然依徐平前世記憶,他們的境内有礦,但開采不出來有什麼用。國際貿易隻能夠使用輕貨,糧食是用不上的。契丹還能夠封起門來過日子?徐平巴不得他們那樣做呢。那樣做的後果,就是周邊的契丹附庸迅速離去,包括燕雲在内,都會不穩,宋朝得利更大。還是那句話,力量對比變了,一切皆變。
契丹喪失了軍事優勢,與宋朝對峙就一切都處于劣勢,沒有翻身的機會。立誓約求和是惟一出路,境況不會迅速惡化,最少還能夠堅持十年八年。要是不求和,各種矛盾就會迅速爆發,最後的結果誰也無法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