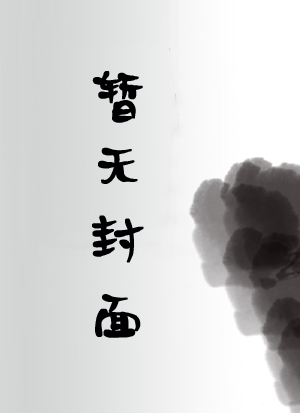在衆人緊張期待的注視之下,灰衣僧人正色開口,“護身靈符乃護身續命的聖物,曆來隻有證道仙班的仙家才得授予,此番交付凡人實屬破例。雖然施主獲勝多有不易,但是按照仙家規章,貧僧還需與您辯法.論道,以辨察心性,确保靈符不會所托非人,若是言語之間有所冒犯,還請施主多多包涵。”
王仕仁拱手說道,“大師言重了,護身靈符非比尋常,轉授之時理應甄辨篩選。”
灰衣僧人點頭過後直涉正題,“請問施主,家中還有何人?”
由于這個問題看似隻是先聊家常,王仕仁便不曾多想,立刻答道,“回大師,在下的雙親早年已經過世,在下為家中獨子,并無兄弟姐妹,亦不曾娶妻生子。”
灰衣僧人緩緩點頭,轉而又問,“請問施主,您為何要趕來昆侖仙宮争取護身靈符?”
灰衣僧人的這個問題王仕仁先前應該也有想過,回答的亦很是幹脆,“回大師,在下乃習武之人,多有行俠仗義之志,濟世救民之心,眼下大唐戰亂四起,天災頻發,朝廷雖有擎天巨臂,護國能臣,奈何大唐地域廣袤,百姓衆多,朝廷總有鞭長莫及之處,各地總有王法漏網之魚,在下有心拾遺補缺,為天下蒼生略盡綿薄。”
王仕仁言罷,灰衣僧人未置可否,而是随口追問,“如此說來,施主争取靈符隻為公義,并無私心?”
眼下争奪的是第八枚靈符,在此之前已經有七位仙家現身,王仕仁一直自場外觀戰,對仙家的行事風格已有所了解,而且他是白鶴觀的俗家弟子,對陰陽天道亦有所涉獵,若是換成其他陰官,他定然知道眼下應該如何回答,但眼前站着的僧人乃是佛門弟子,他不确定自己如何回答才能合對方心意。
拿不定主意,王仕仁便回頭看向長生。
長生很不喜歡給别人出主意,因為任何的決定都會産生相應的後果,隻有承擔後果的當事之人才有資格拿主意,不能承擔後果的旁觀者沒資格說三道四,哪怕是親爹親媽都不應該越俎代庖的替孩子拿主意,更何況是隻有一面之緣的外人。
見長生無有回應,王仕仁隻能回過頭來,“回大師,要說在下全無私心也不盡然,在下有位宿敵仇人,武功高強,修為精深,在下屢次挑戰皆受其辱,故此求取靈符,亦有報仇雪恨,一雪前恥之心。”
灰衣僧人依舊未置可否,随即又問,“佛家有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請問施主,在您看來,放下屠刀,能否立地成佛?”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王仕仁卻是緊張非常,因為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灰衣僧人才會滿意。
王仕仁躊躇之時,台下衆人亦在議論紛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佛門弟子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按理說應該是正确的,但灰衣僧人此時提出這樣的問題貌似太過淺顯,極有可能暗藏變數。
王仕仁關心則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萬般無奈之下隻能再度歪頭看向長生。
長生沒有直視王仕仁,而是轉頭看向大頭,“我認為不能。”
大頭此前并沒有向長生詢問,長生突然開口,他多有意外,急忙撐臂坐直,“啥?”
“因為佛門最重因果。”長生又道。
大頭被長生搞糊塗了,疑惑撓頭,直到發現王仕仁直視長生方才明白長生在假借與自己說話,暗中提醒王仕仁,“哦,對,因果。”
待王仕仁回頭作答,大頭低聲問道,“王爺,您為啥不直接提醒他?”
“因為他不是你們,我若是提醒你們出了差錯,你們不會怪我,但若是提醒他出了差錯,他立刻就會與我反目成仇。”長生随口說道。
大頭點頭說道,“有道理,咱倆說話被他偷聽到了,他就算回答錯了也跟咱們沒關系。”
二人說話之時,王仕仁已經回答了灰衣僧人的問題,隻道放下屠刀無法立地成佛,灰衣僧人追問原因,王仕仁隻道因果循環,報應不爽,若是某人惡貫滿盈,雖然生出悔改之心難能可貴,卻也無法抹殺其先前所做的諸多惡事。
“既然放下屠刀不能立地成佛,佛門弟子為何還會有此一說?”灰衣僧人繼續追問。
王仕仁不是傻子,長生已經給他指出了大的方向,接下來他也就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了,“佛門弟子有此言語,隻為大度寬容,諄諄善誘,正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隻要知錯便不會繼續作惡,隻要知錯便會嘗試補救,遠比将他們拒之門外,令其一錯再錯,越陷越深要好太多。”
“南無阿彌陀佛。”灰衣僧人雙手合十,面露欣慰。
台上二人的對話也令場外衆人多有感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他們都聽過,而大部分人并不認可這句話,因為如果某人奸霪劫掠壞事做盡,到最後放下屠刀立刻就成佛了,對那些一輩子做好事的人來說太不公平,聽得王仕仁和灰衣僧人的話,衆人這才明白佛門弟子之所以經常勸谏壞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隻是為了竭力挽救他們,令他們心生希望并迷途知返,而并不是放下屠刀,就真的能夠立刻成佛。
說這句話的僧尼是不是在撒謊?肯定是,而他們也知道事實并不是自己所說的那樣,明知道自己撒謊會增添惡業,僧尼卻依舊竭力的挽救世人,此舉與地藏王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謀而合,說白了就是隻要你能迷途知返,我們承擔惡業也認了。
“施主如何看待浪子回頭?”灰衣僧人再問。
回答問題最怕摸不清對方的脈絡,隻要摸清了對方的大緻想法,便能有的放矢的進行回答,王仕仁正色說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迷途知返,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