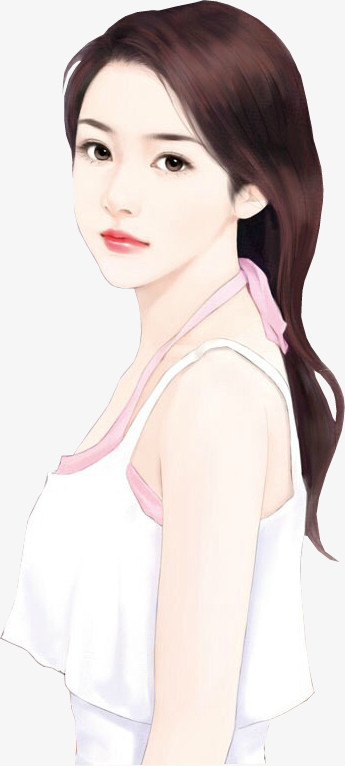龍門境修士顧陌,浮萍劍湖榮暢,一起望向那位剛剛出關的年輕人。
顧陌有些驚訝,一位下五境修士的煉化本命物,動靜太大,氣象太盛,這不合理。
榮暢身為元嬰劍修,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不止是驚訝,是有些震驚。
齊景龍沒有轉身,收起了那座本命飛劍造就而成的小天地,出手之時,不見飛劍,收手之時,仍然不見飛劍。
齊景龍對榮暢說道:“有些失禮了。”
榮暢出身浮萍劍湖,有郦采這種劍仙,門内弟子想要不爽快都難,所以沒有什麼芥蒂,笑道:“能夠親身領教劉先生的本命飛劍,榮幸至極。以後若是有機會,尋一處地方,放開手腳切磋一番。”
齊景龍笑道:“隻要不是在砥砺山就行。”
陳平安走到齊景龍身邊,與隋景澄擦肩而過的時候,輕聲說道:“不用擔心。”
隋景澄心中大定。
好像前輩現身,比劉先生的飛劍一出,還要讓她感到心安。
哪怕她現在已經知道,前輩其實隻是一位下五境修士,境界修為暫時還不如齊景龍。
陳平安站在齊景龍身邊,“謝了。”
齊景龍說道:“真要謝我,就别勸酒。”
陳平安笑道:“好說。”
然後齊景龍将事情緣由經過大緻說了一遍,可知不可道的内幕,自然依然不會說破。陳平安煉化本命物,必須專心緻志,心無旁骛,所以齊景龍四人的對話,陳平安并不清楚。但是荷塘這邊的劍拔弩張,還是會有些模糊的感應。尤其是齊景龍祭出本命飛劍的那一刻,陳平安哪怕當初心神沉浸,依舊清晰感知到了,隻不過與心境相親,非但沒有影響他的煉物,反而類似齊景龍對陳平安的另外一種壓陣。
陳平安轉頭對隋景澄說道:“你先回屋子,有些事情,你知道太早反而不好。我和劉先生,需要與顧仙子和榮劍仙再聊聊。記得别偷聽,涉及你的大道走向,别兒戲。”
隋景澄點點頭,徑直去往自己屋子。
看到這一幕,榮暢心情有些凝重。
陳平安在隋景澄輕輕關門後,不等陳平安說什麼,齊景龍就已經悄無聲息布下一座符陣,在隋景澄房間附近隔絕了聲音和畫面。
随手為之,行雲流水。
極快極穩。
陳平安仿佛也完全沒有提醒齊景龍的意思,關門聲響起和齊景龍畫符之時,就已經望向那兩位聯袂趕來尋找隋景澄的山上仙師,問道:“我和劉先生能不能坐下與你們聊天,可能一時半會兒不會有結果。”
顧陌點了點頭,“随意。”
陳平安坐在齊景龍身後的那條長凳上,齊景龍也跟着坐下,不過稍稍挪步,不再坐在先前的居中位置。
從頭到尾,齊景龍不過是站起身,好好講道理,出劍再收劍。
當兩人落座,榮暢又是心一沉,這兩個青衫男子,怎的如此心境契合?兩人坐在一條長凳上,隻看那落座位置,就有些“你規我矩”的意思。
關于那位姓陳的“金丹劍仙”,這一路追尋隋景澄,除了那些山水邸報洩露的消息,榮暢和顧陌還有過一番深入查探,線索多卻亂,反而雲遮霧繞。
至于劉景龍,完全不用兩人去多查什麼。
北俱蘆洲年輕十人中高居第三的陸地蛟龍,劉景龍,是北方太徽劍宗迅猛崛起的天之驕子。
如今太徽劍宗的兩位劍仙都已遠遊倒懸山,對于一位宗字頭仙家而言,尤其是在一言不合就要生死相向的北俱蘆洲,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以劍修作為立身之本的大山頭,仇家都不會少。
但是沒有任何人小觑沒有劍仙坐鎮的太徽劍宗,修為不夠高的,是不敢,修為夠高的,是不願意。
兩位去往劍氣長城的劍仙,其中一位太徽宗主,不是劉景龍的傳道人,另外一人,輩分更高,也不是劉景龍的護道人,有此機緣的,是劉景龍的一位師姐,但是北俱蘆洲評點十人,并無她的一席之地,因為劉景龍入山之時,她就已經是金丹瓶頸的劍修,劉景龍成名之後,她依舊未能破境,哪怕太徽劍宗封鎖消息,也有小道消息流傳出去,說是這位被寄予厚望的女子金丹劍修,差點走火入魔,還是劉景龍親自出手,以自己身受重傷的代價,幫她渡過一劫。
反觀劉景龍的傳道人,隻是太徽劍宗的一位龍門境老劍修,受限于資質,早早就趨于大道腐朽的可憐境地,已經逝世。
如今看來,這本身就是一件天大的怪事,但是在當年來看,卻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因為劉景龍并非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先天劍胚,在劉景龍上山後的修行之初,太徽劍宗之外的山頭,哪怕是師門内,幾乎都沒有人想到劉景龍的修道之路,可以如此高歌猛進,有一位與太徽劍宗世代交好的劍仙,在劉景龍跻身洞府境,中途榮升為一位鳳毛麟角的祖師堂嫡傳弟子後,對此就有過疑慮,擔心劉景龍的性子太軟綿,根本就是與太徽劍宗的劍道宗旨相悖,很難成材,尤其是那種可以成為宗門大梁的人物,當然事實證明,太徽劍宗破例收取劉景龍作為祖師堂嫡傳,對得不能再對了。
陳平安望向那位太霞一脈的女冠修士,說道:“我是外鄉人,你們應該已經查探清楚,事實上,我來自寶瓶洲。救下隋景澄一事,是偶然。”
榮暢問道:“能否細說?”
陳平安點點頭,便将行亭一役,說了個大概經過。至于觀人修心一事,自然不提半個字。更不談人好人壞,隻說衆人最終行事。
不說浮萍劍湖榮暢,就是脾氣不太好的顧陌,都不擔心此人說謊。
因為這位青衫年輕人身邊坐着一個劉景龍。
哪怕是上五境修士,也可以謊話連篇,真假不定,算計死人不償命。
可是劉景龍注定不會。
以至于能夠成為劉景龍朋友的人,應該也不會。
這就是一個無形的道理,一條無形的規矩。
隻需要劉景龍坐在那裡,哪怕他什麼都不言語。
“我先前曾經以最大惡意揣測,是你拐騙了隋景澄,同時又讓她死心塌地追随你修行,畢竟隋景澄涉世未深,身上又懷有重寶,如金鱗宮那般暴殄天物的手段,落了下乘,其實被我們事後知曉,沒有半點麻煩,反而是像我先前所看到的情景,最為頭疼。”
榮暢聽完之後,坦誠道:“不曾想陳先生早就猜出隋景澄身後的傳道機緣,還給她留了一個傾向于我們的選擇,看來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陳平安說道:“已經說完了我這邊的狀況,你們能不能說一些可以說的?”
榮暢和顧陌對視一眼,都有些為難。
顧陌飄落在小舟之上,盤腿而坐,竟然開始當起了甩手掌櫃,“榮劍仙你來與他們說,我不擅長這些彎彎繞繞,煩死個人。”
榮暢有些無奈,其實顧陌如此作為,還真不好說是她不講義氣,事實上,隋景澄一事,本就是太霞元君李妤仙師在幫他師父郦采劍仙,準确說來,是在幫浮萍劍湖的未來主人,因為郦采肯定要遠遊倒懸山,之所以滞留北俱蘆洲,就是為了等待太霞元君出關,一起攜手去往劍氣長城斬殺大妖。如今李妤仙師不幸兵解離世,師父大概仍然會獨自一人去往倒懸山。而師父早有定論,浮萍劍湖未來坐鎮之人,不是他榮暢,哪怕他跻身了上五境劍修,一樣不是,也不是浮萍劍湖的其餘幾位資曆修為都不錯的老人,隻能是榮暢的那位已經“閉關三十年”的小師妹。
也就是五陵國的那位“隋家玉人”。
榮暢對此沒有心結,更無異議。
相信所有浮萍劍湖修士都是如此,道理很簡單,怕被宗主郦采一巴掌拍死嘛。
太霞一脈,李妤精通好幾種極妙術法,據說是得自火龍真人的道法真傳。
小師妹真身的的确确就在浮萍劍湖閉關悟道,但是在太霞元君的神通駕馭之下,小師妹以一種類似陰神遠遊的姿态,半“轉世”成為了隋景澄,并且不傷隋景澄原有魂魄半點,可以說屋内隋景澄,還是那個老侍郎隋新雨嫡女,卻不是全部。總之,是一種讓榮暢略微深思就要感到頭疼的玄妙境地。至于最終歸屬,小師妹到底是如何借此練劍,榮暢更是懶得多想。
師父郦采當年沒有多說什麼,似乎還多有保留,反正榮暢需要做的,不過是将那個太霞元君兵解離世的大意外,引發隋景澄這邊的小意外給抹去,将隋景澄留在北俱蘆洲,等待師父郦采的跨洲返鄉,那麼他榮暢就可以少挨師父回到師門後的一劍。至于什麼金鱗宮,什麼曹賦,他娘的老子以前聽都沒聽過的玩意兒,榮暢都嫌自己出劍髒了手。
榮暢一番思量後,依舊不願多說,眼前兩位青衫男子,喜歡講道理,也擅長講道理,但是如果這就将他們當做傻子,那就是榮暢自己蠢了。興許自己透露出一點點蛛絲馬迹,就會被他們順藤摸瓜,牽扯出更多的真相,兩個旁觀者,說不定比榮暢還要看得更加深遠。對方未必會以此要挾什麼,可終究不是什麼好事。
在浮萍劍湖有兩件事最要不得,練劍不行,腦瓜子太笨。
不過師父郦采反正看誰都是劍術不成的榆木疙瘩。
師父每次隻要動怒打人,就會忍不住蹦出一句口頭禅,“腦瓜子不靈光,那就往死裡練劍嘛,還好意思偷懶?”
這種道理怎麼講?
于是榮暢小心翼翼醞釀措辭後,說道:“形勢如此,該如何破局才是關鍵。隋景澄明顯已經傾心于陳先生,慧劍斬情絲,說來簡單行來難,以情關情劫作為磨石的劍修,不能說沒有人成功,但是太少。”
陳平安點頭道:“确實如此。”
在藕花福地,春潮宮周肥,或者說是姜尚真,為了幫助好友陸舫破開情關心結,可謂手段疊出,諸多作為,令人發指不說,而且已算人間極緻的冷酷手段,依舊效果不好。陸舫最終沒能跻身十人之列,不單單是輸給了陳平安,事實上,更重要的原因,還是陸舫尚未心境圓滿,哪怕能夠“飛升”離開藕花福地,其實就等于虛耗了六十年光陰。
榮暢問道:“非是問罪于陳先生,隻談現狀,陳先生已經是系鈴人,願不願意當個解鈴人?”
陳平安搖頭道:“難。”
榮暢皺了皺眉頭。
打算修煉閉口禅的顧陌忍不住開口道:“你這是什麼态度?!修道之人,貪戀美色,就落了下乘,還是說你圖謀甚大,幹脆想要與隋景澄結為山上道侶?好嘛,如此一來,就等于跟我們太霞一脈和浮萍劍湖攀上了關系,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盤!”
陳平安依舊搖頭道:“并非如此。”
有些言語,話難聽。
可是願意與人當面說出口,其實都還算好的。
真正難聽的言語,永遠在别人的肚子裡邊,或者躲在陰暗處,陰陽怪氣說上一兩句所謂的中允之言,輕飄飄的,那才是最惡心人的。
齊景龍也點頭道:“很難。”
陳平安突然說道:“我隻說一些可能性,先說兩個極端情況,佛家東渡,逐漸有小乘大乘之分,小破我執不如無我執,隋景澄修心有成,今日之喜歡,變成來年淡然,才是真正的斬斷情絲。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隋景澄情根深種,哪怕遠離我千萬裡,依舊萦繞心扉,任她跻身了上五境,成為了劍仙,出劍都難斬斷。再說兩端之間的可能性,你們兩位,都是山上宗字頭仙家的高人,應該會有一些術法神通,專克情關,專破情劫,但是我覺得隋景澄的心境,我們也要照顧……”
顧陌又開始頭疼,“你能不能說直接點,該怎麼做,需要這麼絮絮叨叨嗎?!”
陳平安望向她,問道:“對于你而言,是一兩次出手的事情,對于隋景澄而言,就是她的一生大道去向和高低,我們多聊幾句算什麼,耐着性子聊幾天又如何?山上修道,不知人間寒暑,這點光陰,很久嗎?!如果今天坐在這裡的,不是我和劉先生,換成其餘兩位境界修為相當的修道之人,你們兩個說不定已經重傷而退了。”
齊景龍淡然道:“是死了。”
陳平安無奈道:“會不會說話?”
齊景龍嗯了一聲,“你繼續。”
陳平安取出兩壺酒,一壺抛給齊景龍,自己打開一壺,喝了一口。齊景龍隻是拎酒卻不喝,是真不愛喝。
榮暢笑了笑。
話難聽。
理是這麼個理。
他其實比較能夠接受。
不過估計顧陌就比較不痛快了。
果不其然,顧陌站起身,冷笑道:“貪生怕死,還會進入太霞一脈?!還下山斬什麼妖除什麼魔?!躲在山上步步登高,豈不省事?都不用遇上你這種人!若是我顧陌死了,不過是死了一個龍門境,可北俱蘆洲卻要死兩個修為更高的王八蛋,這筆買賣,誰虧誰賺?!”
陳平安猶豫了一下,“你自己不虧?”
顧陌破口大罵道:“虧你大爺!”
陳平安也半點不惱,轉頭笑道:“你修為更高,你來講道理。”
齊景龍微笑道:“你脾氣更好,還是你來講吧。”
顧陌一襲“太霞”法袍雙袖飄蕩不已,氣得臉色鐵青,“你們兩個,别墨迹,随便滾出來一個,與我打過一場!”
陳平安說道:“你師門太厲害,我不敢跟你打。”
顧陌氣笑道:“我又不是瘋子,隻與你切磋,不分生死!”
齊景龍微笑道:“撿軟柿子捏,不太善喽。”
顧陌也沒有半點難為情,理所當然道:“又不是斬妖除魔,死便死了。切磋而已,找你劉景龍過招,不是自取其辱嗎?”
顧陌望向那個下五境修士,“你既然裝了一路的金丹劍修,還打過幾場硬仗,連大觀王朝的金身境武夫都輸給你,那個什麼刀客蕭叔夜更被你宰了,我看你也不是什麼軟柿子,你我交手,不涉宗門。”
然後顧陌疑惑道:“你們兩個是不是在嘀咕什麼?”
陳平安點頭道:“在與劉先生詢問,你那件法袍是不是可以抵禦地仙劍修的傾力一劍,所以才如此兇有成竹。劉先生說必須的。”
顧陌大怒道:“臭不要臉!”
榮暢揉了揉眉心。
這都什麼跟什麼啊。
早知道是這麼麻煩的事情,這趟離開浮萍劍湖,自己就該讓别人摻和。
陳平安站起身。
顧陌笑道:“呦,打架之前,要不要再與我唠叨幾句?”
陳平安搖搖頭,“打架期間,不太說話的,得看你有沒有本事讓我開口言語,悄悄換氣了。”
陳平安一跺腳,這棟宅子院牆之上出現了一條若隐若現的雪白蛟龍,光線炸開,無比絢爛,如凡夫俗子驟然擡頭望日,自然刺眼。
榮暢不過是微微眯眼。
顧陌卻是下意識閉上眼睛,然後心知不妙,猛然睜開。
就是一瞬間的事情。
一抹雪白劍光和一道幽綠劍光飛掠而出。
一襲青衫身影驟然消逝,出現在顧陌身側,又迅猛返回原地,輕輕落座。
顧陌站在原地,呆滞片刻,盤腿坐在小舟上,“好吧,我輸了,你繼續講道理,再煩人我也受着。”
這也是榮暢願意與顧陌一路随行、并且雙方關系還不錯的原因。
顧陌似乎後知後覺,怒道:“不對!是劉景龍幫你畫符才占了先手?!”
齊景龍擺擺手道,“與我無關。”
榮暢說道:“與劉先生确實沒有關系。”
顧陌打量了一眼那青衫外鄉人,好奇問道:“你為何會有兩把不是本命飛劍的飛劍?”
陳平安說道:“你好意思說我?”
顧陌咧嘴一笑,“可惜都沒你出劍快,何況不是生死之戰,以命換傷,我又沒毛病,不會做的。”
陳平安心中歎息。
顧陌除了身上那件法袍,其實還藏着兩把飛劍,最少。與自己差不多,都不是劍修本命物。有一把,應該是太霞一脈的家底,第二把,多半是來自浮萍劍湖的饋贈。所以當顧陌的境界越高,尤其是跻身地仙之後,對手就會越頭疼。至于跻身了上五境,就是另外一種光景,一切身外物,都需要追求極緻了,殺力最大,防禦最強,術法最怪,真正壓箱底的本事越可怕,勝算就越大,不
然一切就是錦上添花,比如姜尚真的那麼多件法寶,當然有用,而且很有用,可歸根結底,旗鼓相當的生死厮殺,哪怕分出勝負之後,還是要看那一片柳葉的淬煉程度,來一錘定音,決定雙方生死。
而顧陌能夠一眼看穿初一十五不是劍修本命飛劍,這興許就是一位大宗門子弟的該有眼界。
榮暢開口說道:“當下有一個相對比較穩妥的法子,就是等我師父來到此地,等她見過了隋景澄再說。不知道陳先生和劉先生,願不願意多等一段時日?”
這其實是強人所難了。
相對穩妥,隻是相對榮暢和顧陌而言。
對于眼前這位外鄉人來說,一個不小心,就是生死劫難,并且後患無窮。若是他今天一走了之,留下隋景澄,其實反而省心省力。能夠做到這一步,哪怕師父郦采趕到綠莺國,一樣挑不出毛病,自己的“閉關弟子”喜歡上了别人,難不成還要那個男人幾巴掌打醒小師妹?打得醒嗎?尋常女子興許可以,但是觀看這位隋景澄的一言一行,分明心思玲珑剔透,百轉千回,比起小師妹當年修行路上的直爽,是天壤之别。
所以隋景澄越是浮萍劍湖器重之人,他榮暢的師父修為越高,那麼這位外鄉年輕人就會越危險,因為意外會越大。
之所以榮暢一開始沒有如此建議,是這個說法,很容易讓有機會好好談、慢慢聊的局面,變成一場天經地義的搏命厮殺。
到時候兩人往太徽劍宗一躲。
便是師父郦采,也不會去太徽劍宗找他們。
既不占理,也無意義。
北俱蘆洲修士不是全然不講理,而是人人皆有自己符合一洲風俗的道理,隻不過這邊的道理,跟其它洲不太一樣罷了。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背景通天的外鄉修士,在這邊死無葬身之地,甚至到最後連死在誰手都查不出來。除了皚皚洲财神爺的親弟弟,龍虎山天師府的嫡傳黃紫貴人,其實還有好幾位身份一樣吓人的,隻是消息封鎖,除了宗字頭仙家,再無人知曉罷了,例如其中就有一位文廟副教主的得意弟子。
這些死人身後的大活人,老神仙,哪個家底不厚,拳頭不硬?
但是你們有本事來北俱蘆洲,卷袖子露拳頭試試看?
北俱蘆洲别的不多,就是劍修多,劍仙多!
陳平安心中有了決定,不過沒有說什麼,隻是轉頭望向齊景龍。
齊景龍笑道:“我依舊閑來無事。”
陳平安欲言又止。
齊景龍笑道:“我道理沒講夠,哪怕我講完了,太徽劍宗也有道理要講的。”
陳平安便不再說什麼。
然後陳平安站起身,去敲門。
齊景龍已經随手撤去符陣。
陳平安帶着隋景澄走到荷塘畔,隻要是可以說的,都一一說給她聽。
最後陳平安笑道:“現在你什麼都不用多想,在這個前提之下,有什麼打算?”
隋景澄小聲問道:“不會給前輩和劉先生惹麻煩嗎?”
陳平安搖頭道:“修行路上,隻要自己不去惹是生非,就别怕麻煩找上門。”
顧陌坐在小舟上,比齊景龍更加閑來無事,看似凝視舟外蓮葉,實則一直豎耳聆聽,忍不住翻了個白眼。
不是因為那人說得不合心意,恰恰是她顧陌覺得對方說得還挺有道理,可是對那姓陳的,她從不否認自己有很大的成見,所以才會如此。
隋景澄點點頭,笑道:“那等我見過了那位高人再說?”
陳平安說道:“可以。”
隋景澄有些神色黯然,一雙眼眸中滿是愧疚,她欲語還休。
陳平安皺眉道:“如果處處多想,隻是讓你拖泥帶水,那還想什麼?嫌自己修行進展太快?還是修心一事太過輕松?”
隋景澄哦了一聲。
既不反駁,好像也不反省。
若是換成自己的開山大弟子,陳平安早就一闆栗下去了。
齊景龍依舊坐在原地,非禮勿視,非禮勿聞。
但是修為高,言語清晰入耳,攔不住。
榮暢可能才是那個最苦悶的人。
大局已定,一開始火急火燎的顧陌,反而變成了那個最輕松的人,瞧着那對關系奇怪的男女,竟是覺得有點嚼頭啊。
之後顧陌和榮暢就在這座龍頭渡仙家客棧住下,兩棟宅子都不小。
與那荷塘宅院相距較遠,也算一種小小的誠意,免得被那兩個青衫男子誤認為是不放心他們。
顧陌和榮暢在小院中相對而坐。
顧陌問道:“榮暢,我隻是随便問一句,你真打不過那劉景龍?一招就敗?”
榮暢笑道:“真要厮殺,當然不會輸得這麼慘,不過确實勝算極小。齊景龍與那位外鄉女冠在砥砺山一戰,要麼收手了,要麼就是找到了破境契機。”
顧陌感慨道:“這個劉景龍,真是個怪胎!哪有這麼輕而易舉一路破境的,簡直就是勢如破竹嘛,人比人氣死人。”
榮暢笑道:“若是再去看看劉景龍之前的那兩位,我們豈不是得一頭撞死算數?”
顧陌搖搖頭道:“那倆啊,我是比都不會去比的,念頭都不會有。劉景龍是希望極大,跻身未來的北俱蘆洲山巅之人,但是那兩位,是闆上釘釘了,甚至我一位别脈師伯還斷言,其中一人,将來哪怕去了中土神洲,都有機會跻身那邊的十人之列。”
顧陌突然問道:“郦劍仙去的寶瓶洲,聽說風雪廟劍仙魏晉,和大骊藩王宋長鏡,也都是強人?”
榮暢點頭道:“都很強,大道可期。”
顧陌疑惑道:“魏晉不去說他,可宋長鏡是純粹武夫,走了條斷頭路,大道可期不适用他吧?”
榮暢想起了之前某位站在自己師父身邊還敢吊兒郎當的家夥,那一句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話語,便照搬過來,說道:“大道長生之外,也有大道。”
顧陌笑了笑,“這類話,與我們山門趴地峰上,那些師伯師叔們的言語,有些相像了。”
榮暢不再多說什麼。
畢竟趴地峰是火龍真人那位老神仙的山頭,老真人幾乎從來不理會山門事務,都交予了徒子徒孫們去打理,老真人隻管睡覺。
像顧陌的師父太霞元君,就是修道有成,自己早早開峰,離開了趴地峰,然後收取弟子,開枝散葉。
除了太霞一脈,還有其餘三脈,在北俱蘆洲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桃山一脈尤其精通五雷正法,白雲一脈精通符陣,指玄一脈精通劍道。
但是無一例外,所有在北俱蘆洲闖出偌大名頭的這四位嫡傳弟子,若是談及了恩師的道法傳授,永遠隻說學到了些皮毛而已。
這種客氣話,聽者信不信?
在北俱蘆洲,還真信。
這還不算最誇張的,最讓人無言以對的一個說法,是前些年不知如何流傳出來的,結果很快就傳遍了大半座北俱蘆洲,據說是一位火龍真人某位嫡傳弟子的說法,那位弟子在下山遊曆的時候,與一位拜訪趴地峰的世外高人閑聊,不知道怎麼就“洩露了天機”,說師父曾經親口與他說過,師父覺得自己這輩子最遺憾的事情,就是降妖除魔的本事低了些。
聽聞好像那位弟子還深以為然來着,好在說起此事的時候,小道士倒是沒對他師父如何嫌棄?
許多别處劍仙,都想伸手狠狠按住那嫡傳的腦袋,大聲詢問那個腦子估計有坑的年輕道士,你小子當真不是在說笑話嗎?!
當然問過問題之後,劍仙們還是要笑呵呵禮送出境的。
北俱蘆洲的劍仙,天不怕地不怕,誰都不怕,就怕半個自家人的那位火龍真人。
好在這位老神仙嗜好睡覺,不愛下山。
不過像那位不知所蹤的年輕道士差不多,他們這些個資質不佳的火龍真人嫡傳弟子,趴地峰上還有十數人,都留在了趴地峰那邊結茅修行,說是修行,落在别處宗字頭仙家修士眼中,那就是……混吃等死了。除了他們,還有許多的小道童,畢竟修為再不濟,也都會有自己的弟子。倒是經常能夠聽到不睡覺的火龍真人親自傳道說法,不過似乎依舊不開竅罷了,外界已經很久沒有哪位趴地峰上的弟子徒孫在修行一事上,讓人感到“能不能講點道理”了,總之都白白浪費了那麼大的一份仙家道緣。許多北俱蘆洲的地仙修士,都覺得自己換成任何一個趴地峰的愚鈍道士,早就一路登天,直接去往上五境了。
所以趴地峰是一處讓人很不理解的修道之地,風水靈氣,既不是最好的,待在上邊的嫡傳和嫡傳們的弟子,也多是些怎麼看都大道渺茫的,所以這些道士雖然輩分極高,但是在火龍真人諸脈當中,其實也就是隻剩下輩分高了,而且趴地峰不會與其餘山頭過多往來,加上火龍真人經常閉關……也就是睡覺,太霞白雲數脈的衆多修士,都沒理由跑去湊近乎,所以對于那些動辄就要見面尊稱一聲師伯祖師叔祖的,既不熟悉,也談不上如何親近。
至于趴地峰這個名稱的由來,衆說紛纭。
最玄乎的一個說法,是趴地峰一帶,曾經隐匿着數條境界極高的兇悍蛟龍,被火龍真人路過瞧見了,可能瞧着不太順眼,就一腳一個,全給老真人踩趴下了,不但如此,惡蛟趴地之後,就再沒哪條惡蛟膽敢動彈分毫,老真人決定在那裡結茅之後,讓弟子們運轉神通,從窮山僻壤處搬山運土,那些惡蛟就成為了一條條寂然不動的山脈,據說最少紫诏峰、南華峰和扶搖峰的由來,就是與貨真價實的“龍脈”有關。
至于早年到底被老真人踩趴下幾條惡蛟,天曉得。
榮暢笑問道:“老真人還沒有回來?”
顧陌有些傷感,“還沒呢,若是師祖在山上,我師父肯定就不會兵解離世了。”
榮暢歎息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