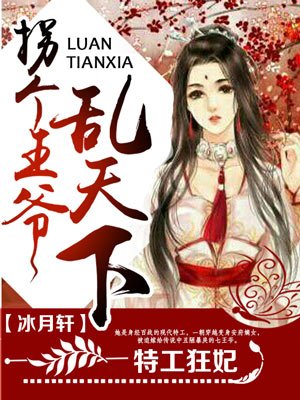一大早,一隻白鴿便從天空盤旋落下,落在了河陰縣鴿塔之上,守哨塔士兵見鴿腿上綁縛着一隻紅色的鴿筒,便急忙解下鴿筒向河陰城外奔去.
河陰城外駐紮着一片大營,約有萬人,這是李慶安的随身衛隊,在和平時期,他出巡的親兵有千人,但在戰争時期,他的随身衛隊便多達上萬人,形成了一支獨立建制的衛軍,稱為虎贲衛,這就是李慶安的警備衛戍隊,包括斥候、騎兵、陌刀軍,共計一萬人整,連續幾天,李慶安都駐紮在河陰縣,他始終在關注相州的戰事,當然,作為一個統領天下大軍的主帥,他不會對相州的結局患得患失,相州守住也好,丢失也好,并不關系大局,郭子儀不是安祿山的對手,他沒有足夠的實力,他李慶安才是。
事實上,李慶安并不關心程千裡的勝負,不關心相州的得失,他現在隻關心一件事,那就是安祿山是否會像他預料的那樣出兵,這關系到他是否能掌控住大局,一旦安祿山真的出兵相州,李慶安便覺得自己開始把握住了安祿山的脈搏,他的一舉一動,他的每一步企圖,都将在他的意料之中。
對于安祿山氣勢洶洶的造反,李慶安一開始并不是非常積極地去應對,隻是消極地防禦,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安西的事情沒有處理完,沒有實力和精力去遏制住安祿山造反。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穿越者,他雖然早在幾年前便知道安史之亂遲早會爆發,但他并不想去阻止安祿山的造反,這并不僅僅是為他個人的私利考慮,而是他知道大唐制度**和土地兼并之烈,大唐社會需要一次像安祿山造反這樣的社會動蕩和沖擊,可以重新進行利益洗牌,可以沖擊士人的思想,可以令當權者進行反思,徹底進行革新,割去腐爛肉,讓大唐重新煥發生機。
而過早将安祿山造反之火撲滅,隻會讓當權者繼續躺在大唐盛世松軟的膿包上,一天天繼續糜爛下去,最後連根子都爛掉。
凡事都有利有弊,關鍵是要控制住一個‘度’,不讓安史之亂烈度擴大,最後像曆史上那樣将整個社會摧毀,成為漢文明千年衰敗的根源,鴉片是毒亦時藥,關鍵是怎麼用?
有時李慶安也覺得自己在賭博,他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唐江山社稷來做賭注。
天剛剛亮,李慶安便習慣性地來到了黃河大堤上,察看黃河的冰凍情況,這兩天,他幾乎每天都要來看了一圈,這是他的一個興趣,老船工說還有七天,黃河将全面封凍,他仿佛就像要驗證老船工的話一樣,每天都要來看一圈,這幾乎成了他的一樁趣事,今天河面上的冰封又向河心延伸了幾裡,一般人已經很難看到水了,隻見河面明晃晃的一片,但李慶安的眼力異于常人,他依然能看清遠處有河水平緩,他甚至能迅速做出判斷,河面已冰封兩裡半,那麼對岸也應差不多,黃河水面寬十裡,已經結冰一半了,這才兩天呢!看來老船工留有餘地,最多五天,黃河就應該全面封凍了,‘黃河初凍莫上行,上行定被龍王請’,這句話他倒是記住了。
“大将軍!”身後遠遠傳來的呼喊聲,李慶安回頭望去,隻見一名騎兵疾速奔來,騎兵翻身下馬,上前行一軍禮道:“河北道情報分堂最新情報!”
報信兵将一管紅色的鴿信筒呈給了李慶安,李慶安将信筒掰斷,從裡面抖出了一卷情報,情報是用安西特别密碼寫成,他随手遞給了身後的親衛,一名親衛迅速将情報翻譯了,對李慶安道:“禀報大将軍,情報的内容是安祿山又親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前鋒已到貝州,與蔡希德軍呼應,共三十萬大軍将圍攻相州,程千裡依然不肯撤軍。”
李慶安的瞳孔收縮為一線,果然被他猜中了,安祿山真正的目的還是要打相州,李慶安暗暗冷笑一聲,其實安祿山還是失策了,他應先該打河東,把相州留給郭子儀,這樣他李慶安的河南軍就不好北上,程千裡的幾萬軍難道還能攻下他的幽州老巢不成?
安祿山攻下相州,就等于直接和他李慶安的軍隊正面交鋒了,再沒有緩沖地帶。
想到這,李慶安回頭令道:“回營,起拔返回洛陽!”
他翻身上馬,向大營而去,剛回到大營門口,卻遠遠看見李光弼飛馳而來,面帶憂慮,李慶安勒住了戰馬,待李光弼近前,他笑道:“這麼急急惶惶而來,發生了什麼大事嗎?”
李光弼抱拳道:“大将軍知道相州之事了麼?”
“嗯!你是說安祿山二十萬大軍南下嗎?我剛剛知曉。”
此時李光弼對李慶安佩服得五體投地,李慶安對大局把握之準,恐怕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安祿山果然大軍南下了,那下一步呢?李光弼更關心他們的對應之策。
“大将軍,安祿山大軍南下,我們該如何應對?”
人大都有一種依賴性,當李慶安将敵軍的行動步步料準後,李光弼便漸漸失去了自主思考能力,開始依靠于李慶安的安排,但李慶安卻希望他能獨擋一面,李慶安沒有多說什麼,隻是笑了笑道:“我隻是來前線考察,并不管作戰,你才是東路軍主帥,該怎麼安排,援助還是不援助,由你自己決定,我要立刻返回洛陽了。”
李光弼呆住了,當李慶安快要進轅門時,他忽然醒悟,連忙道:“大将軍請留步!”
李慶安停住了腳步,回頭笑道:“李将軍還是什麼事嗎?”
李光弼快步上前道:“大将軍,卑職有兩個小小的請求。”
“說吧!你想要什麼?”
“卑職知道河北情報分堂目前就在相州,請大将軍準許卑職和他們聯系,卑職想從他們那裡得到更多、更快的情報。”
“可以!”
李慶安不假思索地答應了,“說第二個要求吧!”
“第二個請求是,卑職想幫程千裡守城。”
“哦?你準備怎麼幫他?”李慶安饒有興緻地問道。
“我想給他們一種新型武器!”
李慶安深深看了李光弼一眼,他放佛從李光弼眼中看到了一種深謀遠慮的思路,便點點頭道:“可以,第二個要求,我也準了。”
.......
蔡希德的三萬前鋒已經殺到了相州,他們并沒有立刻圍城,而是在三十裡外駐紮下來,等待主力到來,盡管安祿山的大軍遠遠未到,但先鋒軍的到來,還是給相州城内吹過了一陣寒風.
相州城内頓時緊張起來,士兵開始晝夜巡邏城池,程千裡組織兩萬軍隊出城開鑿護城河,護城河已經冰凍,失去了護城的作用,但程千裡還是不甘心,他企圖砸開冰塊,不過他很快便放棄了,東城一段砸開沒多久,又重新凝凍了,整個安陽河都凍住了,臨時砸開也隻是白費力氣。
程千裡手忙腳亂,又下令組織民夫将一捆捆箭矢和巨石運送上城,又将四座城門用巨石堵死,護城河上凍,安祿山的大型攻城槌便能直接攻打城門,形勢對他們十分不利。
城防亂作一團,城池中的居民也不平靜了,相州城是河北道僅次于幽州的第二大城,城中原有居民八萬戶,近五十萬人,但在幾次大規模移民及逃亡後,現在隻剩了二萬戶,十萬人左右,盡管如此,十萬人依然是個不小的數目,其中三教九流,無一不有,再加上相州城城池寬闊,想管理好這十萬民衆,也并不是易事。
在相州城中心地帶有一座酒肆,名叫關中酒肆,占地極大,酒肆高四層,可同時容納千名客人用餐,而且前樓後院,還兼做客棧,一向生意興隆,在相州城内也是數一數二。
但随着局勢緊張,這家關中酒肆和其他酒樓一樣,生意開始日漸清淡下來,尤其是它客棧,幾乎沒有客人,相州城内的空房子多得是,不要錢随便住,誰還掏錢住客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