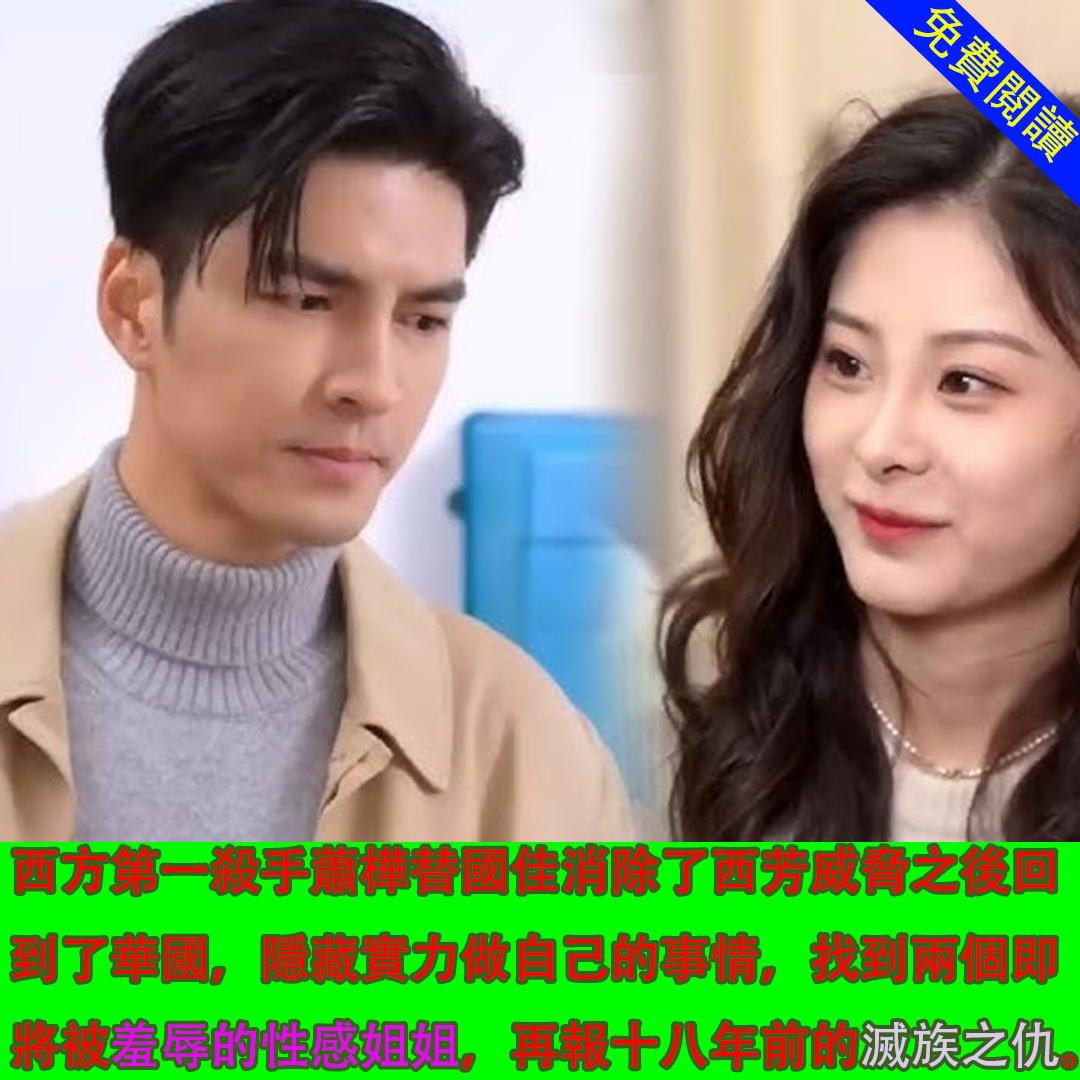白沙城的深夜,大街歸于寂靜。
城北祆祠的聖火徹夜不息,城外的佛寺隐約傳來誦經聲,守捉府後面的打鐵坊裡有燈火,叮叮當當的敲打聲不絕于耳,鐵匠們不是在修補殘損的兵器,也不是在打磨刀槍劍戟,而是在忙着打造鋤頭等農具。
張陵穿上久違的甲胄,手扶橫刀爬上房頂,望着塞外皎潔的月光,面對隐隐約約的大山輪廓和遠處的一馬平川,再回頭看看依然亮着燈的守捉使書房,感慨萬千。
十天前,還是一個誰都可以打罵的奴隸,吃不好穿不暖,過的人不如鬼,生不如死。
而今天不但再次穿上了甲胄,還被委以重任做上了守捉使的親衛。姓名和籍貫寫進了守捉郎名冊,被俘前的軍功照算,依然是酬勳八轉的上輕車都尉!
再次為人,張陵心潮澎湃,暗暗提醒自己這條命是守捉使和韓長史給的,定要誓死效忠守捉使父子。
“老張,房頂上冷,侍禦擔心你着涼,讓你把這個穿上。”親衛隊的隊頭李有為爬上來,遞上一件泛黃的羊皮襖。
韓侍禦現在是從六品下的文官,再過段時間等朝廷的官告下來就是守捉将軍。
将軍如此體恤一個士卒,張陵覺得像是在做夢,心頭一酸,熱淚盈眶。
李有為知道他在突厥那兒遭了好多罪,幫着披上羊皮襖,拍拍他肩膀:“老張,你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侍禦說了,從明天開始讓我們輪流去上葉王村買婆娘,隻要是沒男人的奴婢随便挑。”
“我……我沒錢。”
“沒錢先賒着,回頭從饷裡扣。”
“就算可以賒,買回來我也養不起啊。”
“别擔心,侍禦說了,可以去餘行官那兒先借點錢糧安家,回頭還會給咱們授田,五年不用交賦稅,借的錢糧最多三五年便能還上。”
從做牛做馬的奴隸再次成為大唐邊軍,從一無所有到馬上娶妻生子,張陵覺得一切是那麼地不真實,禁不住掐了掐自個兒的臉,生怕這一切都是夢。
李有為不知道張陵在想什麼,自顧自地說:“别人借錢借糧要利息,咱們去跟餘行官借不用利息,所以該買婆娘就買,該安家先安家,沒啥好擔心的。”
張陵緩過神,下意識問:“不用利息?”
李有為回頭看了看侍禦的書房,感歎道:“其實是要利息的,隻是這利息不用我們給。”
“誰給?”
“長史給,長史你見過的,就是韓侍禦的三公子。其實他一樣沒那麼多錢,這錢也是跟人家借的。他跟人家借錢糧要給利息,把錢糧借給我們卻不收利息。個個說他是瘋子,其實他是菩薩心腸。”
“這怎麼行,韓長史有再多錢也不夠這麼賠的。”
“長史一口唾沫一個釘,他說啥就是啥,我們要是不去借他反倒不高興。”
李有為生怕這個苦盡甘來的老兄不好意思去借錢糧,又擡起胳膊指指四周:“看見沒有,方圓近千裡都是長史的。這白沙城裡以前隻有葉勒王一個主人,不管那些奴隸奴婢,還是那些染坊、紙坊、果子坊、鐵器坊,現在全是長史的。”
原來韓長史家大業大,賠得起。
張陵點點頭,沒有再問。
……
與此同時,韓士枚正在挑燈看餘望裡下午剛整理好的回歸唐人名冊和履曆。
義子幫着解救回的三百二十七個唐人中,有一百九十三個老卒,老卒中又有七十三個老府兵。
韓士枚看完履曆,擡頭歎道:“葉勒部人丁雖不算多,但九族雜居,地域又大,且三面環敵。想把葉勒部治理好,比在關内做州牧都難啊。”
“恩師獨賢,邊之多幸。有恩師在,定能把葉勒部治理好!”餘望裡連忙放下手中的公文,拱手道。
他現在不隻是守捉使府的首席幕僚,而且被韓士枚收為弟子。
奏授的文書已經呈上去了,過不了多久便是白沙守捉城的參軍,經制内的從八品下。
其實想做官很容易,韓平安曾把一錦袋官印倒出來讓他自個兒選,官職最大的是葉勒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
但那是羁縻大都督府的官職,那個從四品下隻是“視同”。
韓士枚覺得這個弟子是安西難得的人才,幫着重新規劃了下入仕之後的路徑,認為弟子要做就做經制内的官,接下來還要好好栽培,送他去長安考進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