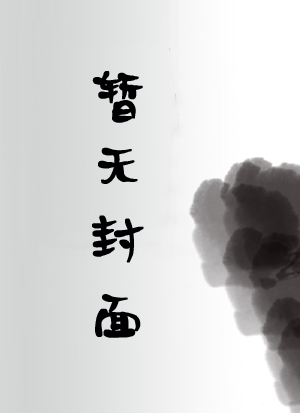我狠狠的盯着蔡京的雙眸,不料這小子也真有過人之處,眼中竟無一絲作僞之色。“蔡元長,朝中之事,非君所宜言。”我沉聲說道。
蔡京似乎有點驚異于我的回答,眼光在那篇《朋黨論》上徘徊良久,忽爾說道:“石相,請恕學生大膽,歐陽公有一句話是沒有說錯的,君子有君子之朋,周家賴以享天下八百年。我讀石相文章詩詞,非古之聖人不能過,石相若能想為大宋建不世之功業,無君子之朋,雖聖人不能成其事。”
我訝異于蔡京有如此的見地,乃含笑說道:“韓念文章蓋世,謝安性情風liu。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杯苦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争占鳌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這一首詞,元長想是聽過?”
蔡京聽我吟出這首詞來,吃驚不小,這是他上任途中在一個官員家喝酒,命一個歌妓依韻而作,這詞說的是他們蔡家兩兄弟同中進士的殊榮。此時我讀出來這首詞來,其意甚明,他弟弟蔡卞深得王安石賞識,他此時有投靠我之意,不給我一個說法,我自然難以相信。
“石相取笑了,那不過是歌妓戲作,實在慚愧。倒是學生平素愛讀三國,聞得昔日諸葛瑾為江東重臣而諸葛亮為蜀漢之相,二者皆能忠心不二,先國後家,常常感歎不已,心裡很向往古人的風采。”
他這是借諸葛家的事情來表明态度,有些話不便明言,隻得如此。這些話是題中應有之義,說到此處,我也知道來此的用意了,定是在王安石那裡不得意,想從我這裡來攀一個前程。蔡京這種人,聰明有之,隻是功利心太重,有時候就愛走些歪門邪道,不過做為一個現代人,我倒不是太反感,水至清則無魚,這個道理我還是明白的。
但是對于蔡京的話,我卻不好正面回答,便拐彎說道:“諸葛兄弟各為敵國,不得已之事,不足為法,國朝蘇轼轼轍兩位大人同殿為朝,共同效忠陛下,正是你家兄弟效法的榜樣。”
這中間也有一層意思,須知道蘇轍進制置三司條例司,怎麼算也是變法派中的中央機構,而蘇轼卻不得意,不得不去做地方官……蔡京是個一點就透的人物,知道我駁回他的話,是為了免得落人口實,當下恭身說道:“學生謹記石相教誨。”
當此之時,因着這新法與舊法之争,大宋多少兄弟分途,朋友反目,這蔡京和他弟弟各走各的道路,倒也不足深怪。我也知道和蔡京打太極打到這個時候,就得讓他揭開那層紙了,他既然要攀附于我,自然身上就得打上“石”字鉻記,否則我怎麼會當他自己人?但是我的實誠話,那就看我高不高興給了,這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别。
我招呼家人把那張《朋黨論》拿去裱好,又把蔡京請入内堂重新坐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方問道:“元長任地方也有一段時間了,可和我說說新法在地方的實行情況如何?”
這是考較功夫的時候了,倘若他說新法好話,那自是不用談了;但即便是他盡說新法壞話,我也不會太看重他,我當他人才用還是奴才用,便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蔡京豈有不明此理的,抱拳說道:“此事本非學生所應當說的。但是石相見詢,不敢不答,一言以弊之,擾民而已。”
“哦?”
“大宋建國百餘年,積弊日多,後人因循守舊,亦無複太祖、太宗皇帝開拓進取之心,對外又屢困于北夷,故此自仁宗皇帝在位之時,朝野便有變法之心。仁宗皇帝特為範公開天章閣,是有慶曆新政,其中主持人物,今日尚在。以仁宗皇帝之明,範公、富公諸大人之賢,慶曆新政,數年便告失敗,後人總結經驗,都知是慶曆新政,關系到大宋上上下下數以萬計的官員的利害,這許多的冗官冗兵,便是大宋建國百餘年來最大的禍害,朝野非不知也,然知易行難,便以範公之賢,亦有所不能……”
蔡京侃侃而談,見我略有贊賞之意,喝了口茶,清清喉嚨繼續說道:“……王相公自熙甯二年入相,号稱天下人望十餘年,上至皇上與諸士大夫,下至黎庶百姓,無不希望王相公能夠一洗大宋百年的頹廢,創中興之功,可以說,當今之世,無人不盼變法……”
我心裡一動,這一層倒是我沒有想到的。便聽蔡京繼續說道:“然天下士大夫于變法的态度有三:其一,号稱人臣楷模的司馬光司馬大人等人,因為慶曆新政的失敗,便認為凡事當小心謹慎,以不變應萬變,雖謂不變,司馬公等人心中的不變,不過卻是走回慶曆新政的路子,不過是更加小心與保守罷了,并非是全然不變;其二,便是王相所倡,以為方今之政,不僅要變,且要大變、急變,他們心憂國朝積弊數十年,希望所有的弊政一朝能改,恨不得數年之内,便可國富民強,盡複漢唐之地,而王相的法度,不過就是避開吏治,以法治國,以為終不以庸吏而壞良法,卻不知道古人曾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此王相之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