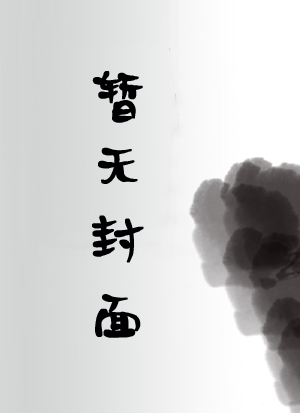趙祯到位子上坐下來,看着不遠處的燈火出神。
讀聖賢書要看其原文,要了解其本意,這話聽起來好像是很正确,但隻是好像而已。從孟子說出這句話,經過後世一代一代人的演繹,早已經有了更豐富的内涵。聖賢之所以是聖賢,不僅僅是由于他們是那一個時代的傑出人物,更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累積了千百年來多少人的沉澱,那是能說剝去就能剝去的?
徐平去從《孟子》原文來解釋這個“利”字,明白說還是托古改制的那一套。趙祯自小由名師教導,受過良好的教育,哪裡還不明白這個道理。
孟子解詩,強調要“以意逆志”,徐平所說,是符合這個原則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趙祯在仔細思考中間的利弊得失,而沒有直接出口反駁。
從王安石,到追随他的改革派,之所以把孟子擡起來,其實跟韓愈提孟子道統的目的和立場有細微的不同。王安石等人尊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意逆志”這個四個字,是托古改制進行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以己之意,而逆推古聖賢之志,實際上就把秦漢以下的儒家經典全部抛開,相當于另起爐竈。
孟子雖然迂闊,他的理論也大多不符合當時的實際,但根本上,他是以一個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曆史舞台上的。對于當時的各國是如此,對于儒家就更加是如此。他的這個改革者的特性,才是他從諸子被擡起來進入孔廟的原因。
一直到北宋末年,孟子最主要的标簽就是改革旗幟,随着改革的失敗而慢慢喪失這一光環。至于後來,進了孔廟的孟子,自然就任由打扮,他本來如何已經不重要了。
徐平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年代人們心中的孟子,跟自己前世是有很大不同的,對李觏極端反對孟子的态度很猶豫。畢竟,自己也是改革者,總是要有一塊招牌。這樣一塊招牌是借用這麼一位古人,還是去另行打造,還要在實踐中摸索,由實踐給出答案。
思考良久,趙祯吐出一口氣:“于國有利之事自然很多,但以錢糧為綱,此話隻要一出朕口,必然天下鼎沸!此事容後再議,不由朕口,更加不能着于诏書,且先一步一步來吧。要改朝政,我們先從容易做的開始。”
徐平的心裡也出了一口氣,他不怕趙祯擱置起來,時間畢竟是在自己一邊的。他怕的是趙祯直接跟自己辨論,說到底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呢。
向趙祯拱手,徐平道:“陛下謹慎,正是以天下蒼生為念。臣尚年幼,經過的世事還不多,所思未必周全。在陛下身邊且學且做,且做且學,慢慢來總是好的。”
趙祯點頭,面色也緩和下來:“此事朕可以不說,但你在三司,管的就是天下錢糧,可以放手去做。真闖出事來,有朕擔當!你我二人攜手,也勝過無數無用書生!”
“謝陛下恩典!隻是如此重任落在臣的身上,卻如泰山壓頂,隻怕臣擔不起。”
趙祯笑道:“我擔得起,你自然就擔得起!”
說完,趙祯指了指身邊的位子,讓徐平坐了下來。
徐平謝恩坐下,又道:“隻要手裡有了錢糧,天下的百姓衣食無憂,國内便就無大事。至于外部,此時契丹也是新君繼位不久,當無大變。隻有黨項,現在看來早晚會鬧出大亂子。不過黨項那裡,小瞧了自然不可以,其傾國之兵,據說可以有數十萬之衆,陝西河東兩路壓力極大。但也不至于過于高估他們,黨項終究是小國,地瘠人貧,引動朝廷的也不過是兩路之地。打仗打的就是錢糧,隻要朝廷錢糧充足,熬上幾年也能熬死他們。最怕的其實不是黨項的軍事威脅,還是由此消耗的巨額錢糧,外亂引起内亂。說到底,隻要府庫充盈,内外都不足懼!”
“不錯,隻要有錢糧在手,天下可走!可是,徐平,我是天子,天子要有天子之德,必須要以仁德治理天下。我也知道錢糧很重要,但對于天子來說,這永遠不是最重要的。你在邕州以通判提舉蔗糖務,提舉溪峒事,權知州,入京為判官,為鹽鐵副使,除了提舉溪峒治理蠻族,都是在跟錢糧在打交道。你的為人做事我已經知曉,不會讓你做兩制詞臣,哼,那個想做你也做不來啊!在诏書敕令上,你敢寫一句以錢糧為綱,我可以容你,文武百官絕容不了你!以後,你還是老老實實在三司吧。”
“臣明白,臣要學的确實還有很多!”
兩制詞臣代為起草诏書敕令,文采好隻是基本要求,還要求有政治敏感性。亂寫一句話,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晏殊也是當過參知政事的人,還不是因為當年為翰林學士的時候寫李宸妃制詞沒有政治敏感性,一下就被撸掉了,現在還升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