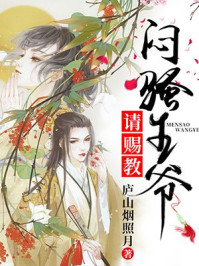忽必烈大怒,将弓擲于地上,左右怯薛縱馬奔出,去獵那觸怒龍顔的鹿,十幾名弓馬娴熟的怯薛一頓操作猛如虎,連一根鹿毛都沒射到,那頭神秘的公鹿竟然失蹤在草海之中,隻打了幾隻肥兔子。
而大汗已經意興闌珊,撥馬回去了。
草原上的城市夏日裡充滿了涼爽的風,宏偉空曠的的宮殿和廣場略帶蒼涼的感覺,出了城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原,城市裡滿是駱駝和羊,忽必烈在宮中都能嗅到那股熟悉的牲畜腥臊味道,這也是家鄉的感覺。
他經常暢想,在江南精緻華麗的宮殿裡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有朝一日他的軍隊會進入臨安,接受宋皇的投降,他的士兵會在臨安的皇宮裡喂馬,将巨幅的綢緞帳幔扯下來包裹在身上,就像他們在西域的城市做的那樣,本來他以為,這一天會在今年發生,現在看來有些過分樂觀了。
忽必烈準備返回上都,畢竟那裡距離南方更近,便于指揮調度,他并不是很着急,他不相信宋軍敢逆襲,就算暫時失去一些疆域,他也能迅速收回來。
何況在大都還有一整套完備高效的行政機構在正常運作,有他心愛的嫡子真金太子,還有他寵信的宰相阿合馬。
大元皇帝尚未動身,另一個人已經來到了大都,看着這座與重慶臨安上海都迥異的雄渾北方帝都,他渾身每個汗毛都倒豎起來,是激動,是緊張,是彷徨,是兼而有之。
他是窦林卿,前重慶聖母堂秘書監掌印官,充軍發配至膠州軍營做賊配軍,後因作戰勇猛被擢升為校尉,又随韓青至益都建功立業,本以為就在軍中發展了,沒想到突然收到軍統司的調令,另有重任在身。
窦林卿換了身份,他現在的名字叫王著,是李齊政權的一名軍官,益都大族出身,張弘範打過來的時候,王家全族投效,王著被封為千戶,後韓青帶兵殺來,将王家滅門,王著隻身逃走,颠沛流離來到大都。
寬闊筆直的街頭,一輛馬車緩緩而過,窦林卿看到馬車上的徽記,眯眯眼,跟了上去,車簾打開,丢出一包東西,窦林卿撿起來,到僻靜處打開,是一套蒙古钹笠帽和長袍腰帶靴子,裡面夾着一張紙,寫着時間地址。
窦林卿換上衣服,去了紙上标明的地方,那是個茶館,一幫文人墨客正在談古論今,這種事情窦林卿擅長啊,他當即加入,侃侃而談,一番言論令人歎服,其中一人問他尊姓大名。
“益都王著。”窦林卿說。
“在下關漢卿。”那人也通名報姓。
……
臨安,運河畔,一大片夯土結實的平地上,無數人頭湧動,這是禦前三大營校場,現在是白龍新軍兩萬義烏兵的練兵場。
劉骁帶着副官來視察軍訓,一幹人等站在司令台上眺望滾滾煙塵,所謂司令台其實就是一個土壘的高台,上面搭着遮陽棚,可以俯瞰整個校場。
趙官家看的津津有味,他長在深宮中,何曾見過這些玩意,所以無論練兵練得多麼稀奇古怪,他都不會覺得奇葩。
但是一些樞密院官員就不同了,白龍新軍的練兵方式和禦營大軍區别甚大,總結起來就一句話,騎自行車翻山越嶺打槍放炮。
劉骁打造這支軍隊是用于華北平原作戰的,适合騎兵馳騁的地形,自行車基本上也能勝任,所以士兵的核心訓練都是圍繞自行車展開的。
先是紀律和體能,每天枯燥的隊列和十裡長跑,單雙杠,俯卧撐,背誦軍紀條目,然後是上課學認字,可以不會寫,但不能不認字,基礎文化訓練後學自行車原理,拆裝,補胎,修車,騎車帶人,騎車開槍等,整個的訓練科目都是當年從網上下的瑞士自行車部隊訓練大綱修改而成。
訓練中發現的好苗子,會被保薦到武學進修,經過半年學習,出來就能穿官靴,當排子頭,挂校尉銅牌。
劉骁嘴上說不急,心中明白兵貴神速,要和忽必烈搶時間,等義務兵訓練好,大都也準備妥了,優勢就沒了,所以他早早就開始了動作。
上兵伐謀,這是每個看過一點書的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實際能達到這個層次的人少之又少,陰謀詭計在國戰面前隻能徒增笑耳,真正的上等計謀,永遠是陽謀。
劉骁在崇明之戰後就開始布局,派了大批人員滲透北方,軍統司本來就在北方安插了許多耳目,每個州縣都有情報站,有的甚至暗藏了十幾年,也不需要探聽什麼機密消息,就做個普通人就行。
……
從臨安向北九百裡,有一個地方叫楚州,在金國與宋并立之時,楚州地處前線,戰争頻繁,幾度易手,時至今日,這裡的百姓做大元朝子民已經數十年了。
在楚州城北有一戶殷實人家,姓代,代老爺膝下隻有一女,十年前找了個贅婿,原來姓什麼已經不重要,這贅婿改姓代,依舊用本名,就叫代昆,字日比,原是個逃難的孤兒,入贅之後風生水起,開了一爿布店,專營南方走私來的松江棉布,生意紅火,沒幾年就起了新宅,添了車馬,成為楚州城的翹楚人物。
早晨,代昆起床後先去後院給老太爺問安,照例是要跪在地上聽老頭子教訓的,代老爺對這個贅婿并不滿意,一來沒生兒子,十年才生了兩個閨女,二來不老老實實種地,做起了布匹生意,士農工商,商賈的地位是最低的,他惱恨女婿把自己的門風都給帶偏了。
代老爺說:“姑爺,我們代家世世代代都是種田的本分人,未曾出過買賣人,别覺得掙了幾個銅闆,就把尾巴翹到天上去,開布莊終究不是個體面營生,攢下些本錢,還是要多多置地才是。”
代昆唯唯諾諾,隻說爹爹見教的是,小婿無甚本事,勉強做點買賣糊口也是情非得已,等過了年就不做了。
給老泰山磕完頭,代昆回自己屋吃早飯,老婆不動筷子,他就不能動,這老婆也是個奇葩,長得醜不說,臉上還有一個大黑記,脾氣也暴躁,生了兩個女兒滿腹怨氣,隻說代昆種子不好。
“若不是我家收留你,你早就變成路邊的餓殍了。”這是老婆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
代昆笑笑,不予反駁,吃罷了早飯,出門上了轎子,臉上的表情就變了,從受氣包變成了殺伐果決的大掌櫃,他先來到布店看賬目,聽取大夥計彙報,然後去城裡茶館沏上一壺茶,聽父老們談論家長裡短。
十年來,楚州城的一切盡在代昆的腦海中,有多少兵馬,多少錢糧,帶兵的千戶住在哪兒,家裡幾口人,知州大人喜歡吃什麼喝什麼,夫人是哪裡人士,城市布局,山川地貌,哪裡能渡河,哪裡有水井,他閉着眼睛都能畫出來寫出來,這些并非絕密軍情,但也不是一朝一夕能獲取的,需得水磨工夫才行。
從茶館出來,代昆去了一趟城隍廟,這裡比較荒僻,沒什麼路人,在城隍廟後面的小樹林裡,他見到一個老朋友。
“啥時候是個頭?”代昆說,“起初說三年,後來又說三年,這都三個三年了,你别說還得三年。”
那人道:“用不了三年,海門大捷,元軍損兵十萬,王師就要北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