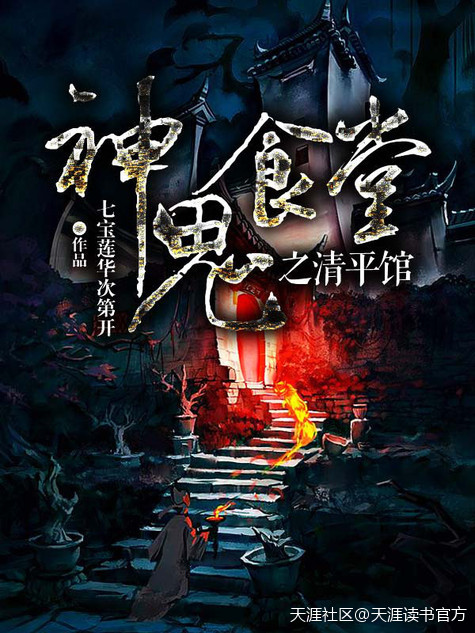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四百三十三回國破山河應有恨,城門自問恨何人
那少年年約十七八,颀長白皙,頭戴雲冠,綠绨袍,風姿龍采,音如玉箫,本該有雙眼悲憤,此刻卻滿目清明,直視着面前那大漢,一字一頓,仿佛那大漢并非什麼豪傑之人,而是他的臣工,語氣之中,帶着一種不容違抗的凝重:
那少年說:“汝不可驚我祖宗陵寝。”
那少年說:“汝速以禮葬我父皇母後。”
那少年說:“汝不可殺戮我百姓。”
那大漢皆是應諾,開口言,願封其為宋王。
“暖風熏得遊人醉,隻把杭州當汴州,宋王?呵呵。”那少年突然一笑,頓時一張臉上,如銀瓶乍破,迸出滿室珠玉,“燕山亭猶在,這樣的溫柔和夢,孤卻是從來不做的。”
“大膽,闖王面前!你一個黃口小兒如何能自稱為孤!”一個虬髯大漢喝聲而道。
李自成擡了擡手,轉向那如珠似玉的少年:“汝可知,汝家何以失天下?”
那少年又是略帶嘲諷地一笑:“汝盡可問百官,百官當知。”
那虬髯大漢啐了一口,道:“你們當皇帝的,護不住江山,怪什麼百官!”
那少年伸出雙手,那手白皙如玉,五指如洞箫,他似乎想要說什麼,但又不想再說什麼,隻是又看了一眼李自成,要拔足離開。
倒是李自成開口道:“既如此,天色已晚,不如你我同坐,共飲一杯。”
那少年眸光驟冷,盯着李自成看了許久,而後突然一笑,笑得寒光萬劍似地,直看得身經百戰的李自成也心中擂鼓,才淡淡回絕:“國喪家孝,不必了。”
說罷,他不顧左右皆是冷刀寒劍,大步流星地走了。
“你們去看住他,我總覺得這個太子不一般。”李自成對左右說道。
“小毛孩兒而已。”
如是過了數日,崇祯以禮大葬,李自成聽聞太子日夜以淚洗面,足不出戶,亦不吃不喝,可他卻百事纏身,無暇顧及,便随意将太子封為宋王,命人嚴加看管。
紫禁城很大。
朱慈烺一直是知道的,譬如他每日晨起讀書,随父皇上朝,皆是不可以坐車駕,要自己走去的。父皇嚴格,母後雖然心疼,卻不敢寬慈。從小他就知道,盡管出身皇家,身為太子,未來的國君,可本朝的皇帝,不提昏庸之輩,但凡有能為者,無不是夙興夜寐的,若非如此,怎有先祖孝宗勞極而死,宣宗早生華發。
所以朱慈烺從不曾抱怨風寒雪大,步足辛苦。
可是,紫禁城這麼大,大得他已經無處可去了。
朱慈烺擡頭看着金屋紅瓦,這宮阙深深之中,他的影子顯得如此渺小,正如那不可違抗的巨輪滾滾向前,将山河碾為齑粉,他不過是齑粉之一,亦是如此渺小。
城破了,将降了,家亡了,人死了。
那麼一個少年太子,算什麼呢。
朱慈烺覺得自己這個時候的心緒,也是很有趣的。
他竟然還勾了勾嘴角,笑了笑,就仿佛另外有一個他,冷眼看着這些,這些他做夢都想不到會發生的事情,看着日夜禁不住眼淚長流的自己,一個人如玉質,在此刻卻百無一用的自己——這一切另外那個他都知道,就像是已經寫好的宿命。
他甚至知道,李自成也會失敗。
鶴蚌相争,漁翁得利,李自成敗走以後,亦會将他擄走。
然後……
“然後,你作為朱慈烺的命運,就該結束了。”一個熟悉的聲音,溫柔地說。
朱慈烺猛地轉過身,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這人眉目溫和,正是他記憶之中那人,可這人的眉目太過溫和,面容太過年輕,已經不是他記憶裡那憔悴勞累的模樣。
“父皇……?”朱慈烺震驚地看着眼前的人。
這人,正是他的父親,崇祯帝朱由檢。
朱慈烺本能地收住了自己想要上前的腳步。
如若眼前這人,是他的父皇,那陵寝之中長眠,又是何人?
朱慈烺自問這短暫數十年,見過不少奇異,曾被疑為天目鬼瞳,可再見許多,那也是旁人之鬼,他山之怪,他可以無動于衷,然而這人,是他的父皇,不,是他的父親。
為他的出生驚喜不已,他剛一歲就封他為太子,親手教習詩歌書法,傳授他為人為君之道的父親。
朱慈烺向前邁了一步,隻覺得腳下仿佛踏着刀鋒,這一步走得如此心痛。
“父皇……”朱慈烺伸出手來。
“我不是你的父皇,或者說,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你的父皇。”朱砂苦笑,“萬歲山抛下江山家國,抛下你自缢之後,我便沒有資格做你的父皇了。”
朱慈烺握緊雙拳:“那父皇為何不帶我走。”
朱砂伸出手,想要摸摸朱慈烺的發旋,正如眼前這個少年還幼小的時候,他曾經經常做的那樣,可那手上,五指間黑紅兩色纏繞婉轉,仿佛是畫上去的符咒一般,那是魔君的證據,魔族的皿緣。
朱砂還是放下手去:“我不能。或者,當時我也有一線癡念。”癡念着,也許你可以複興山河,癡念着,也許你可以隐居田園。
我雖是一位帝王,但終究也是一個父親。
朱砂低下頭。
朱慈烺心口起伏,顯然此刻心緒不甯,翻起無數波濤潮湧,找不到出口,不知如何應答。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緻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朱砂突然開口,“這是我臨死前寫下的話。”
“李自成……告訴我的,似乎有些不同。”朱慈烺微微皺眉。
“這話,雖然一字未差,但前後有誤。”朱砂擡頭看着藍紫色的,漂亮得不似真而似幻的天空,“我寫的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雖皆諸臣誤朕,然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緻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朱慈烺猛地擡頭:“那李賊所言,便是如此。”
朱砂一笑,頗為雲淡風輕:“身死之際,心有愧恨,神思頓悟,又能如何。上面我先說的,與你聽到的不同。那是因為,上面我說的那一段,是後人編撰。我身後以亡國之君,遭人唾棄,皆是因為,我至死還在責怪臣工。”
“然而他們并非無辜。”朱慈烺低頭。
“是啊。不過我也不是無辜之人。隻是我們所有人,都阻擋不了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那是我們的宿命。”朱砂看着藍紫天空裡,那歪着頭的俊美男子和笑得頗有幾分肆意的女郎。
“這句話,不知為何,我仿佛聽過。”朱慈烺凝眸,“我們所有人,在曆史的洪流面前不過是蝼蟻,注定将被那巨輪碾為齑粉。”
“是你自己告訴你自己的嗎?”朱砂問。
朱慈烺一震,脫口而出:“父親您為何——”
“因為那是你的本心。那是因為你從一出生,就注定與烜兒不同。”朱砂看着朱慈烺,“你的孿生弟弟朱慈烜,本該是你。”
“啊?”朱慈烺有點懂,但又不敢相信。
“周氏有孕,彼時太醫并未查出雙生之相,後難産,生出孿生兄弟,一是你,一是烜兒。因為難産,輾轉太久,烜兒天生不足,艱難掙紮,還是去了,你卻是神完氣足。”朱砂一笑,“當時我多高興。因為太醫曾經告訴我,皇後胎相極其兇險,這一胎必定不保。我自知會失去烜兒,但未料還有你。我很感激,你這十幾年,是我的孩子。”
“可是……”朱慈烺覺得自己又變成了兩個人,一個人震驚不已,一個人卻恍然大悟,一個人覺得天降雷鼓,一個人覺得果然如此。
“你是風神之子,風神為上古洪荒之神,生而為風,是純粹的思想精神,因此風神注定以凡人的身份出生,曆經磨難,化作天邊羽翼,乘雲而去。這是風神的宿命,無人能違。”朱砂解釋道,“你的父親跟我說,你隻要一聽到,就會明白了。”
朱慈烺捂住心口,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那本該劇烈跳動的激動,此時此刻,卻突然變得十分平靜,他竟然是十分平靜,一點兒也沒有驚訝和震動地,接受了這件事情。就仿佛他一直知道,一直在等待這個驗證。
“萬歲山,我抛棄一切自缢之後,心懷怨憤,立地成魔。與同我一起成魔的左右,墜入魔界,成為魔君之一,自名朱砂。從那一刻起,我就已經不是你的父親了。朱由檢,是朱慈烺的父親。而南琪,才是現在的你的名字。朱砂并非南琪的父親,而是南琪的朋友,親人。南琪的父親,本名南喬,上古風神。不過有意思的是,你的這位父親,與老朱家也頗有幾分淵源,他也曾為大明的齊王,名為朱能垣。”朱砂笑着看着朱慈烺。
“是他!”朱慈烺突然想起自己曾經看過的雜記,那名為《琪花瑤草》的雜叙手記,來自明代藩王齊王手書,裡面記載的無一不是一些趣聞轶事,一些飲食起居的精細喜樂,詩詞歌賦,雪月風花,彼時他不過是十一二歲,正是喜歡這些雜記的時候,還曾有些羨慕這位齊王,作為藩王,遊山玩水,自得其樂。
“說這麼多,其實還是百聞不如一見。”朱砂看着朱慈烺,“十五日後,便是太子朱慈烺走失之時,此後史載,再無你的名字。因為這是曆史的節點,不可更改的命運之輪。這一日朱慈烺注定失蹤,而你,将會成為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