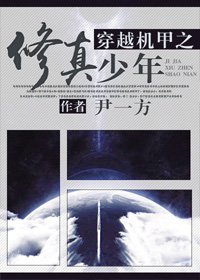張曜宗其實對于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不是說你穿越了說幾個GOODIDEAS古人就對你點頭納拜了。古人厚黑起來也不弱于後人,唐朝有個古人宋之問為了搶自己親侄子的一句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強索不成就用大土坨裝袋壓在侄子兇口把侄子壓死了。趙瑗就是以後的宋孝宗趙昚,是南宋最有作為的皇帝,張曜宗從來沒有奢望趙瑗會對自己言聽計從。點頭納拜。這幾個主意不被人搶走就是好的了。
自己現在所有的做法都是為了引起趙瑗對自己的興趣,所說的幾個主意沒有一個是可以輕輕松松就能做成的,都需要高層政策以及大量的人手和财力才能做到,以趙瑗現在的力量是根本沒有可能的,但是現在不給趙瑗打好防疫針讓他心裡有個數,将來就更難以做到。
趙瑗,不,是宋孝宗,他将來的經曆證明,宋孝宗是一個心有大志,但容易猶豫變化的人,立志北伐,但是手下已經沒有像嶽飛,韓世忠那樣有才能的能臣了。先是用李顯忠和鄒宏淵進行隆興北伐,鄒宏淵度量狹小,嫉妒李顯忠的軍功,拒不增援李顯忠另隆興北伐失敗。從此宋孝宗做事就有點瞻前顧後,更是學會了左右平衡,為了防止一黨獨大就算重虞允文這樣的能臣,也同時用主和派為丞相,虞允文也因為懼怕宋孝宗的左右搖擺而不敢出川抗金,最後病死川中。此後宋孝宗抗金再無可用之将,也就從抗金的理想派轉為了現實派,從此不提北伐,安心發展國内經濟。
自己現在所能做的就是引起趙瑗對自己的欣賞,潛移默化的改變趙瑗的性格,更是要樹立趙瑗的信心,不再搖擺不定。現在的趙瑗還沒有經曆隆興北伐,心智還算堅定。從今天自己的表現和趙瑗的反應看來,自己顯然已經引起了趙瑗的欣賞。還是那句話,張曜宗不敢以為這樣就真的可以馬上影響趙瑗了,趙瑗畢竟是未來的皇帝,老趙家的皇帝真沒哪個是笨蛋,不然被人把骨頭吃了都不知道,現在自己最大的優勢就是年齡,年齡小,趙瑗可以認為張曜宗可以被早早施恩,收歸己用,也更加放心。宋孝宗還念舊喜歡使用舊人,史浩不說了,那是孝宗的老師,就是潛邸的兩個下級官員曾觌,龍大淵也備受重用,如果自己早投趙瑗,将來可能也會得一個幸進的名頭,但是現在也顧不上了。隻要現在自己能夠得趙瑗賞識,自己也就可以潛移默化的影響趙瑗。劣勢也是年齡小,年齡小代表着現在無處可用,說的話可能不會被人重視。
總的來說今天已經是成功的了,至于今晚沿着趙瑗的興緻還能談多少能入趙瑗耳朵的東西,張曜宗也沒有計劃,談到哪是哪吧。但是從今天說話也要注意分寸,之前可以肆無忌憚的狂言,是為了引起注意,但是到了别人手下還是口出狂言就是找死,君不見曹操手下的楊修。自古名士皆狂士其實都是為了引起别人注意。
“不知王爺今晚興之所在?還望王爺起個頭?”史浩問道。
趙瑗沉思片刻,“孤之志在于北伐,不若就沿着北伐衆議吧!”因為韓世忠也在場,趙瑗就找了個韓世忠能參與的話題,但這也正是趙瑗最大的心願。
韓世忠首先說道:“暫且不論官家是否還有北伐的意思,但是現在北伐可謂困難重重,西軍富平一去,我大宋禁軍幾無可戰之力。能戰者不過張俊,嶽鵬舉,吳玠,劉光世,韓某等寥寥數人,如今鵬舉已去,光世,韓某去職,僅餘張俊,吳玠,吳玠知川路。張俊?哼。”
韓世忠冷哼一聲,對張俊不予置評,但是言辭中的不屑之意再明顯不過了。
“良臣啊,你和伯英之間的龌龊我也有所耳聞,但大業當前,你們就不能聯手抗敵了嗎?”
“不瞞王爺,和張俊的矛盾我老韓可以不在乎,隻要官家願意北伐,不管是讓我做張俊的馬前卒還是押送糧草,我老韓一句怨言都不會有。我韓某人不屑某人可以不與他相交就行了,但是事情輕重我老韓還是分的清的。隻怕官家久久不願北伐,我老韓就沒那麼長的命去等待了。”韓世忠言之鑿鑿。
趙瑗和史浩不禁贊道:“韓将軍兇懷博大啊,真乃大丈夫也。”
“韓元帥的意思是北伐無望嗎?”趙瑗的臉色有點暗淡。如果韓世忠不看好北伐,自己還沒有多少軍事經驗,難道就不能收複汴梁?複太祖偉業了嗎?
“臣沒有這樣說,王爺,我的意思也是今晚早些時候曜宗所說,我軍現在守土有餘,進取不足,如若北伐,為帥者需好好甄選,士卒也許好好操練,更重要的是要上下一心。”韓世忠連忙解釋說:“我老韓一心都在北伐上,如果王爺北伐,韓某一定效死。”
趙瑗聽了韓世忠的解釋臉色才有些放緩。
史浩說:“官家孤騎南渡,可謂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一面收羅北地殘兵敗将,死死頂住金賊進攻,另一面再立朝廷,整理亂局,收攏各部勢力,可謂功在社稷。惠澤千秋。”
趙瑗和韓世忠都點頭稱是。張曜宗實在沒勇氣跟着附和。他年齡小,倒也沒引起趙瑗和韓世忠的注意。唯有史浩又盯着張曜宗問:“光世以為如何啊?”
張曜宗暗罵史浩,硬着頭皮點頭稱是,繼而說:“小子雖小,但也知道官家功績,更是與民生息,才有我紹興中興。雖富平一役西軍殆盡,但依然有我師傅與嶽伯伯等一幹強軍,為什麼官家不繼續北伐,恭迎二帝呢?”
張曜宗幹脆直指人心,看史浩怎麼回答這個千古疑問。你敢說趙構不想迎回二帝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嗎?讓你難為我。
史浩呐呐無言,這個問題不知多少人想過,但是誰敢問。除了嶽飛那個傻子不但問還寫詩“行複三關迎三聖,金酋席卷盡擒歸。”怎能不讓官家記恨。
“光世啊,官家沒有不想恭迎二聖,實在是時機問題。富平一役,西軍殆盡,種家再無可用之人,苗劉之變,楊幺作亂……南方亂局未定,官家實在是無暇北伐啊。”也隻有趙瑗能這樣為趙構辯護。
張曜宗本就不願就此事跟趙瑗辯論,這事你知道你猜都行,就是不能說出來,剛才已經不冷靜了,為了噎史浩就脫口而出,要知道趙瑗将來的谥号可是孝宗啊,他對于把他扶上皇位的高宗趙構可謂真的是以孝侍人。跟他辯論趙構就是自找沒趣。
“草民不敬,還望王爺海涵。宣和皇後,建炎皇後都還在北地,官家自然心存北伐之心,隻是時機不成熟。”張曜宗解釋一下還不忘刺一下趙構,你媽和你媳婦都還在金人手上,你自己在南方做皇帝威風,還記得她們嗎?但這都是事實,他人也無從辯駁。
“草民以為,北伐須将帥一心。将知兵,兵知将。自太祖杯酒釋兵權後,領兵大将三年一換五年一換,所以禁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因此雖禁軍人數衆多,但沒有有效指揮,沒有發揮作用,非士卒無用。出西軍一直跟西夏鏖戰,頗為勇悍外,其餘衆軍已失其威。然富平一役,依然指揮失當,令大好局面毀于一旦,甚是可惜。”
“光世,不要總拿太祖說事,往事已矣,你隻說以後該怎麼辦?”趙瑗攔着張曜宗的話頭。
“王爺,我沒說太祖的不是,時移勢移,太祖立國亦是以武立國,先滅後蜀,再滅南唐吳越,也是功高蓋世。但是太祖壯志未酬,太宗繼太祖遺志,可惜功敗垂成。我大宋北有大遼,西有西夏,吐蕃,可謂強敵環顧。一直沒有收回燕雲十六州可謂我大宋的遺憾。我大宋缺馬,馬政卻一直沒有成效。更兼抑武揚文,百年間防禦有餘,進攻不足。名将隻有守土之能,卻無開拓疆域之神将。此亦為二因。三則政堂不清,想我大宋初年,名相如雲,趙普,寇準,晏幾道,韓琦,富弼,文彥博……”
“光世怎麼沒有提範文正公(範仲淹)和王文公(王安石)和溫國公(司馬光)啊?”趙瑗納悶,此三人也是大宋名相,名聲甚至高過前面的數人。
“王爺,仁宗陛下初起用範文正,不可謂不急切也,範文正卻對人言‘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可見文正公雖有改革大緻,而審慎回翔未敢輕舉。可謂辜負聖心否?及至仁宗陛下‘一日特開天章閣,诏對賜坐,給筆劄,使當面書奏’文正公才‘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然文正公的改革措施卻止‘澄清吏治,厚農桑,修戎備,減徭役。’而已,可謂循序漸進,然已負仁宗厚望。即便如此,文正公亦被诟病。”
“王文公‘夫合天下之衆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則阡陌闾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争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号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後世之紛紛乎?’罪天下民而依然未成。”張曜宗說的也有些口幹,喝了一口香茗,清香入口,分外惬意。
“光世,你接着說。”趙瑗急着問道。剛才說的,都是自己知道的,但是沒有想那麼多,聽張曜宗的意思,他還有更深的理解,慶曆變法,王安石變法都是北宋時期影響深遠的事件,如果真能被張曜宗找出病因所在,那麼就可有的放矢。也許會取得成功。
“範文正,王文公皆可稱為君子,然君子為卻各有不同,範文正行動不迫切,止隔靴搔癢亦被責難,何也?得罪了既得利益者。王文公更甚,不止既得利益者,更兼平民亦被王文公所傷。範王政策于國家有益乎?然也。何不能成?家國天下,有些人把家看的比國更重。此也可謂私心。誠然,人無私心天誅地滅,然國之不存,個人何以家為?”
“光世語直抵人心啊。家國天下,家就真的比國重要嗎?”趙瑗沉思說道。
“但文正公和王文公為何不入光世法眼?不能稱為名相?”史浩問道。心中暗說:“難道你還能比範仲淹和王安石更有作為嗎?”
“史大人嚴重了,小子不敢評判先賢,隻個人意見。文正公對上未解君憂,對下舉措不利。此可謂兩頭不讨好。王文公為行大志,止用小人,為此神宗避開政事堂,中旨任用。此一壞我大宋百年傳統,太祖共士大夫共治天下休矣。此二開我大宋黨争之先河。”張曜宗此言就有些大不敬了,對于王安石的增強皇權有異議。
“光世此言是否有些過了,神宗先祖不過也是為了行新策増國力。并非成心違太祖共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趙瑗不得不解釋。
“太祖曾言共士大夫共治天下,天下群臣方能以天下為己任,萊國公(寇準)更敢直犯龍顔指摘天子不是,及至王安石,小人當道,壞我百年君子之道。再至徽宗陛下,蔡京,高俅,童貫更不能言為君子,蔡京雖有茶法改革,歲增财賦。然蔡京更謀私利。高俅更是嫉賢妒能,童貫欺上瞞下,一閹人居然封王,除晚唐宦官之禍時,古未有之。宣和四年,攻遼失敗更以百萬貫從金人手中贖下燕京,妄言大勝,曝己短于金人,招緻後禍,此皆王安石開任用小人先河所緻。”張曜宗點出王安石的錯誤。
“至于溫國公,雖聲名顯赫,但從未曆地方主政值守,空談有餘,實幹不足。更兼開元祐黨争之先河。毀安石公數年心皿于一旦。我西軍瀝皿所得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司馬光居然割讓給西夏。此為大不智,更難言名相。”張曜宗越說越氣憤,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得了四寨居然輕易還給西夏,簡直是弱智。
韓世忠也是憤憤不已。如若四寨在手,西軍即可放牧西疆,安西都護府更可拒敵于國門外,因為司馬光的不智,毀西軍心皿萬千。
張曜宗一番話讓衆人贊歎不已,抽絲剝繭将兩次變法不成的原因和所造成的影響都點了出來,可謂深刻,更兼指出了皇權獨大,少了士大夫的制衡後所帶來的小人當道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