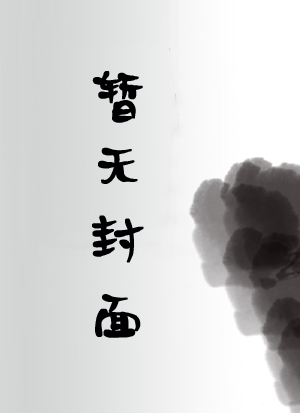我很詳細的考慮了終結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産生的後果,王安石一定會以辭職來應對的。而我又不能夠在此時出掌宰執之位,在内心的深處,我認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擋箭牌。我記得魯迅有一個著名的譬喻,在中國,倘你說要在屋子裡開一扇窗,必然有人出來反對,你這窗是開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聲叫着要把這屋都拆了,那麼拆窗的主張就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雖然是變革,但總比拆屋要溫和得多。王安石對我的用處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為他新法為國庫斂财的本質,可以保證國庫的充盈,為以後的大變革做準備,而我不必承擔斂财的惡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擾得紛紛擾擾的新法,就可以讓保守派們向我靠攏,從而使我一些溫和而務實的改革措拖得以順利的推行。
倘若沒有了王安石,隻怕保守派就會分裂,一些有識之士固然會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卻一定會維護他本層的利益的。我并不願意面對這樣的一種局勢,政治有多兇險,讀多了史書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頭都對準了我,那麼我的出身與來曆,我的年輕,甚至我至今未娶,都會成為攻擊我的借口,流言會分化民衆對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會得罪許多的民衆。而我承認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個階層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個力量夠強的階層,僅憑借着皇帝對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無法在政壇上站穩腳跟的。特别是這個皇帝,曆史曾經證明過他并不是一個很堅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這個宰相的位置上,幫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後由我來做好人。打一個壞壞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個強盜,搶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當,然後我來做好人,還給他們一半的家當,或者隻搶走他們一半的家當,人們比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後,心理上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我了。這是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我豈有不利用之理?
因為王韶在西夏邊境創辦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而市易法的危害還沒有顯示出來,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會引發一場朝會中的大辯論,而辯論的結果若是我的政見獲勝,則必然讓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辭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則即便皇帝信任我,隻怕他也無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況且這個年輕皇帝的信任,絕對不可能是無條件的,這一點我一直牢記在心。
兩種結果皆非我所樂見,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還是集中精力攻擊免役法,順帶着把市易法給斃了,同時再對保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擊免役法卻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辭職,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種新的政策來取代免役法。畢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成,毫不誇張的說,免役法構成了王安石斂财的主要手段。
鑒于這種情勢,第二天,我請皇帝召王安石入宮,做一個小規模的讨論。因為以我的身份,是沒有辦法和宰相辯論國家大事的,否則與禮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個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的大臣來,簽署了一份诏書,給了我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沒有宰相的副署,視為無效,不具備法律效應。而隻要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給了我這個宰相銜,并特許我不必參預朝會,雖然祖制所無,但是眼下根本沒有人來得及阻止這一道閃電任命。而事後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這個任命視為一種恩寵來解釋,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銜做為一種恩寵賜給元老大臣。
所以當王安石進宮之後,我已經是大宋國名義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臉色很不好看,很明顯,他已經知道我從昨天入宮一直沒有回家,而一進來皇帝就向他宣布了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國公布了,朝報上面也會有這樣的消息,想阻止也來不及了。我有點擔心那些給事中們,他們沒有駁回這道诏書,王安石肯定會記住他們的。不過政治鬥争總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沒辦法……
王安石聽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簡直就是悖然大怒,不過礙于皇帝的臉面,才不好發作。他的道理倒是講得很明白,無非是免役法有多麼精密,國庫每年的淨入達到二三百萬貫,而我則死死的攻擊免役法擾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對國富與民富的辯證觀點。因為我準備得相當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舊黨一樣,隻是泛泛而談,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實事例,有地點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統計數字,指出免役法對百姓的禍害有多深;王安石對此根本無法解釋,到最後他竟然賴起皮來,說這種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這樣的現象。我知道這種辯論手段他也曾玩過,沒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氣的追問:“相公謂不能保其無此,然某請問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賣屋交役錢,相公可能實證?”順便還給他帶了頂帽子,“某亦敢問相公,之前百姓賣屋納稅,是仁宗皇帝時呢,還是太祖皇帝時?又因何事所緻?”又批評他:“相公為宰相,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而謂不能保其無此,此非宰相之過耶?”